电厂老员工汪学山早先就是个银匠,汪师傅言语不多,是个非常勤奋、对工作十分负责的锅炉工。上班时因为人工输煤、炉前看火,上三班制,一个夜班下来非常辛苦、也很劳累。工友知道他是祖传的银匠手艺,家有小孩满月、周岁等,请汪师傅打副带铃铛的银手镯、脚镯或做一副“长命锁”,汪师傅是有求必应。下了夜班,囫囵睡了一会,翻身爬起来,拎过着火的炭炉子,来到小柜桌前,把装着银料的坩埚放进炉中,让银料在炭火中渐渐熔化。这边从柜子抽屉里取出一个模子,看不出是铁还是什么材料,从中掰开,黑呼呼两面一样的格局。汪师傅找出一毛刷在上面刷了刷重新合上。在炉子上的坩埚加了点不知什么油,锅里的银水突然沸腾起来。汪师傅拿过一把夹钳,夹起坩埚斜着精准地倒向模具,真有卖油郎倒油进瓶一条线的功夫,待模口有料溢出立即收住,又将坩埚放进炉中。冷却后从模具中取出“长命锁”,去除毛刺、用什锦锉刀修磨、抛光后,精巧、锃亮的银具让人爱不释手。
过去有钱的人家嫁女儿,聚媳妇会送祖传戒指、金、玉镯或珠宝类物件。但大多数人家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能给女儿或新媳妇打一副银镯就很不错了。汪师傅做活最多的就是打银手镯,具体操作是怎样的细节,应该不是我上面所说的那么简单。头脑中银匠就是敲敲打打的映像,直到退休那年厂里组织的一次“云南之旅”,给我补上了这一课。
丽江市的华坪县有个新华村,是个白族人聚集的地方。白族姑娘的服饰非常漂亮,特别是那美丽的银制头饰更是让人叹为观止。依仗丰富的银矿资源,这里很自然地成为中国的“银都”,也是来丽江游客的必到之地。村里的银器展卖厅都有大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琳瑯满目的头饰、银器让人目不睱接。和同事王奎华,买了一只同样的银戒子作为纪念之外,也实在受不了那吵吵嚷嚷、人挤人的环境,和陈国一起出得场外,信步来到对面的村街里。
不愧为银都,街面上偶尔见到两、三家饭店、旅馆外,清一色地都是门前挂着“X X银匠铺”、或X X――百年老店,用金水、银水扫字的黑底招牌。门面有大有小,估计也是寸土寸金之地。银铺里地上、桌上到处摆的是银板银条的料品,好像铁匠铺里的铁块、铁钉一样,扔在哪里都很随意,让我感觉有点怀疑和惊讶,这哪像是成品后都十多块钱一克的待遇啊?
一小伙子正在铁镦上,用铁锤砸着一根银条,“乒乒乓乓”地砸得很起劲。有点不解,只好揑住嗓子,窝起舌头和小伙说起让他还能听懂的普通话。原来是做成品的银料一定要熟,银料必须经过无数次的锤砸,才能去除杂质,使银条变软有绵性。此时,另外一个约50岁左右的中年人也坐到一小桌前,拿一根已砸熟的银条放进一沟状模具中,点着一盏喷灯,嘴里含一弯头吹管,深吸一口气,用嘴吹气将火苗变成一道细线转移到银条上。银条在蓝色的火焰中渐渐变软,用小锤轻拍,将其平复在沟槽里。待银条稍微冷却后,取出放进同样宽窄带花纹的模具中,仔细敲打、拍平,力量始终如一,毫不停留地一路敲到头。再从模中取出,精心弯曲成圈,钢印轻敲做上自家店铺的记号,美仑美奂的银手镯就出现在中年人的手中。
师傅很热情,好像也是炫耀,同样憋着劲,蜷着舌头、操着当地的普通话告诉我,手工制作与机器压模,显示出厚重和呆板的不同。外行的我似乎也看出些许差别,不管怎样,老师傅锤打成品的那种专注,使产品无一点缩、涨不匀的现象,说明他已经掌握了本行技术的真谛。
东坎老街还有几家例西街中部陈姓的银匠铺,大多打造戒指、带铃铛的脚镯、手镯等,也做小孩满月、端午节佩带在脖颈上大项圈。
双游里巷头,有家很有名的“董记银匠铺”,店主董二爹故世较早,董二奶和我岳母是几十年的老朋友。我结婚那年,岳母家因地方小,“回门饭”都是在董二奶全家帮助下操办的。董二奶人很善良,为人直爽、一手拉扯多个子女,但生活再难,也喜欢说个笑话,是个十分的能干人。因为文化大革命,好多被资为封建迷信的银器具不能做。但也因为“文革”,1967年左右利用自家门面,做起了时兴的毛主席像章。那段时间,董二奶真是个大忙人,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模具和学来的技术,竟然把主席像章制作的像模像样,大的、小的品种齐全。用不是银,却是铝为原料做出来的像章,大受群众的欢迎。再兼印些“红卫兵”袖章、旗标,更是忙得不亦乐乎。那段时间,董家全家上阵,也请同行帮忙,浇铸的景象紧张忙碌,引得许多路人驻足观看。
银匠们联未联社且不去说,但那时的计量社,也一定是有的。计量社址就在“鱼市口”南巷、百货公司西天井的大门里。儿时“躲蒙找找”的小友“二杀猪”和“三扣眼”的老爸吴德元、正红中学老师彭广成的父亲等都是计量社成员。早先的彭家与老街图书馆斜对面,和边上另一家秤店,都是做杆秤为主。做秤的情景,每天上学、放学就能见到。
彭老师家老店位于“鱼市口”巷西第三家,座北朝南,一间门面也是作坊。一张小凳摆在屋中,凳子旁边的地方摆着木尺。一把钻孔的钻子,立着的铁杆上有一方木槽,夹上铁钉敲扁的钻头,另外一手柄的木杆,用牛皮绳绕着几圈与钻杆连接。钻头放在木头上,扯动十字型的木杆手柄,一通狠搓,秤杆上就能钻出对通的洞来。秤杆大小不一,有钩秤,盘秤,秤砣也是五花八门,都是生铁铸造,有的很粗糙,小秤砣还算光滑精致,大多还有铸家的记号。
秤是计量的主要器具,对人们的生活也很重要,几乎是每家必备。腌个萝卜干、咸菜放多少盐,甚至买了煤屑做炭饼,要放多少泥土掺拌都能用得着。买个粮、买个菜,心生怀疑,怕错了大花子(大数),被人短了秤,用自家的秤一称,便知分晓。过去的人绝大多数还是讲诚信的,买卖之间都少有发生坑买坑卖的行为。偶有上门兜售之人,曾被人揭露过短秤之事,再与交易,买者也会警告:“秤要足啊,我要告(校)秤?”。卖者一定会说:“你佬放心,不行,就拿你家秤来称”。好像也很大度,交易成了,也重新建立了信任。
做秤的人家在门面的边上都放一木桶,里面插着多根车制好的秤杆。秤杆都是一头粗、一头稍细,有的大秤能达到1多米长,最粗的刀口处都有5公分粗细,能秤几百斤的重量,大都用于农村称大肥猪和秤粮、分草等。扁担穿进秤上一粗铁丝的环里,大秤钩起梱好的物体,两人抬起秤来,一人将秤砣在秤杆上移动,物体与秤砣间使秤杆持平,吊着秤砣的绳系定在某个秤花段,即能知晓所秤物品的重量,秤越大,称量的数量越大。市场买卖、家庭用秤大都能称二、三十斤也就足够了。药店秤药的小戥子,小巧精致也是秤。
做秤的人从桶中抽过一根小秤杆,用一细木砂纸包着,在秤杆上下摩擦,把个秤杆摩得水滑。一把圆规在一尺子上量个尺寸,分开两脚在秤杆上转过来一点、转过去一戳很快等份到头。再偏转一下,同样在秤杆上做好等份。拿过一支削得很尖的铅笔,在秤杆上的点上重新描戳一下,杆上的星花便清晰可见。一个不大的手钻,同样是牛皮筋连成的十字架样,钻头很尖很细,在秤花上依次钻过去,动作急而准,就像在秤杆上绣花般地很快完成。在秤头两侧再钻上三分之一深孔,装上可拎秤的“刀口”,系上一根绳配上秤砣,用天平校秤后,在5、10或10、20……斤处标出数字,依样再在相邻约两、三公分的位置,装上称量大的刀口,再行校验。其间,还需对秤杆油漆、秤星装饰、秤尾包铜等多道工序后,秤就做成了。
吴德元不做杆秤,专门修理磅秤。上世纪六十年初东坎街才有的磅秤,改变了用大秤抬着计量的景况。除了秤面的铜牌外,基本都是铸铁制造,很重。每当听到老街里有“嗗碌嗗碌”铁轱辘与条石的摩擦声,就能知道这是推着磅秤移动的声响。吴师傅也可以说是老街修磅秤第一人,家里通常有个一、两座待修的磅秤,修理什么东西我们小孩也不懂。因为经常在“二杀猪”家玩,对磅板下那四角放着的小铁球和象石锁一样25斤、50斤不等的砝码很感兴趣,对吴师傅能修先进的磅秤很是敬佩。
今天是5月16日,从新闻中获知也是“世界计量日”,又是一种巧遇,借此回忆一下在现今菜市场仍在使用着的小秤,觉得很有意思。
写“十大社”,从开始的心中没底,生怕写不全,到今天已经写了十一社。究竟写成的有哪些不是当年的十社成员,还有哪些是社员的未写进来,到现在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自我安慰一下,恐怕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的事,也没有多少人能说清。其实也无所谓,拙以为记出来的是手工业范畴应该都可以。为了弥补可能的不足,再简单叙述一下老街里是手工,也是服务业的照相馆作以填充吧。
老街里的照相馆在老街“鱼市口”西侧,座北朝南,和老图书馆对门。一间门面靠西设一柜台,作照像人交费和取片的地方。后面的照相室用一紫色布帘遮挡,撩起门帘迎面一幅油彩大画布,画着的一圆门,一泓碧水,荷花莲池,很是清新好看。三条腿支撑的攝影机蒙着一块里黑外紫的绒布,立在背景图对面约两米的地方。攝影室屋子不大,拉一顶棚,看起来比较清爽,两侧窗户一样用紫绒布遮挡。
一对拍结婚照的青年在柜上开了票,顺便浏览一下门里的样照,一前一后进了里间。一个瘦削尖下巴、满脸带笑的中年师傅迎了上来,接过照像的小票看了一眼,便安排两人坐到装饰后成条石样的凳子上,男左女右。被唤着沈二爷的师傅退后一步,端祥了一下,踏步上前,扳下男士肩膀让其坐正,让女士挨着男的再近些。转身来到攝影机前,打开镜盖,一对新人的影像,就倒着出现在机器一块几厘米宽长的玻璃镜上。沈二爷头顶着机盖布,看着影像指挥着,调整照相者的坐姿和表情。有时再走过去对男或女拨拨脸或挪一下身体,让女士做出一付倚偎感的小鸟依人模样。一声:“就这样,不要动了”,快步回到机前,从机旁的布袋取出一块有两三层样的方木匣子,插进带槽的紫(音)口内,从中往上一抽,层叠复杂的木匣遮没了影像,沈二爷重又把黑紫绒布顶在头上,干着外人不得见的事,顺手抓起机右侧一橡皮球,朝照相的两人说:“好,嗳,就这样,眼睛不要眨,表情自然些”。被折腾半天的青年紧张的大气不敢喘,加之那年代的人受“男女授受不清”观念影响,大庭广众之下怎能放得开,哪里还谈得上自然。沈二爷只好又说一声:“笑一笑”,手一握橡皮球,好了。拍照之人深呼一口气,如释重负。
小孩百日、周岁,照相馆也会预备婴儿凳、小木马、铃铛、皮球等小道具。孩子去当兵,全家拍张全家照作纪念。老人大寿,四世同堂拍张“全家福”更是难得。照相馆有时也出外景,1960年,外公召集全家人在“工商联”后,李笃斋家有着枸杞花开背景的院子里,拍了几张全家福和各家的照片。三十多人的全家福,把个沈二爷忙里忙外,辛苦的不行。距今近六十年,己经泛黄的老照片成了全家人珍贵的回忆,更被当作家传至宝。
新建南路“爱好者攝影部”王玉霞的爸爸个子很高,也是照像馆的攝影好手。因为不是本地人,融外地很多先进经验,照相、洗片技术都很强。照相社里还有老曹和以后的高开等攝影师。也是亲戚的梁贯和我三哥李开汛虽没有照相的专业技术,却也做些管理或开票、发片等杂务。
随着前河南部的发展,老街的照相馆也迁至县电影院南侧、紧挨着闻名全国的长画廊。新馆大门两侧设很大的玻璃窗,展示着大幅美女素颜照,很是吸引人的眼球。迎着大门的柜台开票取片。到影院看电影候场的人,没事也去会瞅两眼大橱窗的照片,进到馆内看人家拍照的人也不在少数。不知道拍照片的到底有多少人,但表象上看起来是顾客盈门,很热闹。
新馆的背景墙又大也有变换,新增一台依然是三角架子的老式攝影机器。拍单人照片时,攝像师也开始用挂在胸前的“海鸥”牌照相机拍照,方便也快捷,但所拍的照片都是黑白的。橱窗内展示的彩色照片也都是水彩描画,有点浓妆艳抹的味道,看也好看,却不真实。尽管如此,滨海也从此有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照相馆。
统观全篇,手工业还有“匠”可写,例皮匠;服务业还有“社”可叙,例茶社等。写到这里,已经超过了开篇初衷的“十大社”,虽意犹未尽,却也有点疲倦了。需要说明的是,所有记述的内容对我来说,因为都是行外之人,文中定有不少行外话,甚至错误,谢谢大家关注的同时,敬请广大读者指教、见谅。
我们这一辈人,经历了老东坎街手工业由盛到衰的过程,也见证了这些行业由落后到先进、由手工到机械化、智能化的进步,亦喜亦忧。喜的是生产力的提高,少了多少人的吃辛受苦;忧的是,上古千年、很多优秀手工中所包含的文化遗存,终将被人遗忘。
作者:李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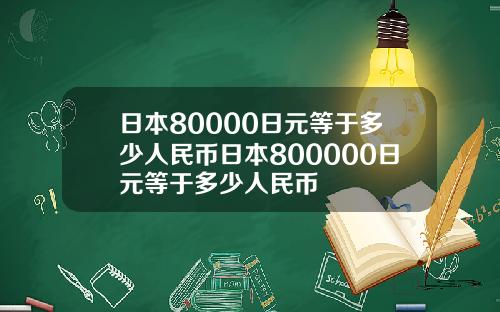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