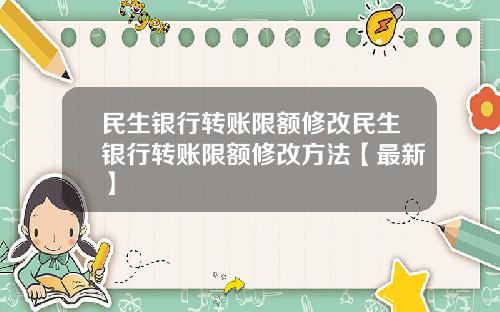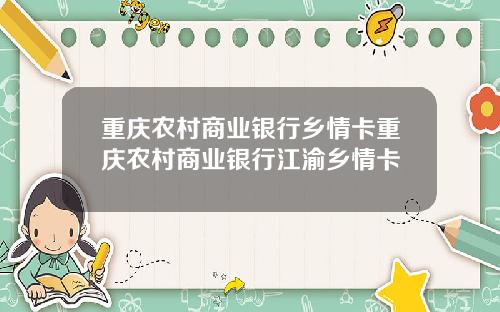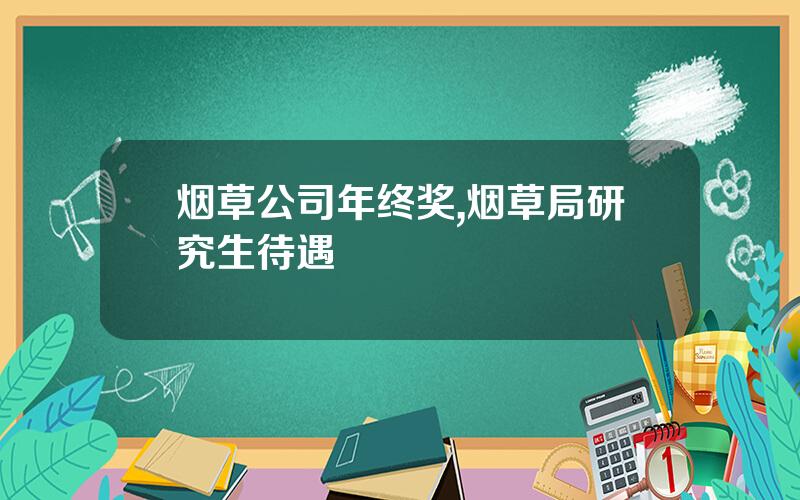留在儿时记忆里的,是过年时在被烟熏黑了的门楣上,映衬着大红的对联透着喜庆劲儿在煮肉的香气中摇曳着的五颜六色的门钱儿。灵动的景象就那么鲜艳的投射在心灵的记忆里,那时候物质很匮乏,心灵却很丰富。那一个个意味深长的习俗、一件件透出吉祥的饰品把年深深地刻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让我们回想起来,常温常新!
这样的年好像离我们已经很久了。 我们沉浸在现代的视听与化学的包装中,那乡土的大红大绿、老生老气已经逐渐被我们遗忘了。
而门钱却没有离我们远去,依旧在乡村的某个角落顽强的展示着他茁壮的生命力,大红大绿地装点着每一个我们童年时的新年。
博兴篇:刻染门钱粗犷大气
□朱庆光 李振平 田中岳
这是博兴县曹王镇曹王二村,鲁北平原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村落。
55岁的曹金祥和他的一辈辈长者,就在这里用他们那因用力变了形的拇指和一把把自制的凿刀,为人们刻染出出一方方妆点年味的罗门钱,招摇在春节时每家每户的门楣,呼唤着丰收与喜庆。
质朴的曹金祥和大多数艺人一样,岁月的流逝只把一门手艺存留下来,而寄托在上面的文化基因,早已在谋生的艰辛里被抛出记忆之外。除了用技艺与刻刀来表达以外,曹金祥已经说不出这传承已久的门钱的来龙去脉。
相比起其他地区的门钱,流行在博兴一带的门钱更拙朴一些,多是用黄白毛头纸或仿纸凿刻而成,再以红黄绿三色手工染色而成,颜色自然生成,富于变换,大红大绿中透出鲁北的粗犷与大气。
在曹金祥的家庭作坊里,我们目睹了门钱的凿刻染色过程。
曹金祥说,做门钱用的纸,以前多是南方的手工纸,古时用来练书法写大仿的仿纸,它柔韧,渗透性好,染色时鲜艳,是从淄川买进的。而现在多是机制的没有漂色的原生纸,相比起来,对颜色的渗透力要差一些。
纸是论刀的,一刀约在200张左右。做门钱时,需要先把纸裁开,一张纸约能裁15打左右。
首先按照门钱的基本尺寸,用铅笔在纸上打上线格,然后在线隔开的纸四周钻上眼,用自制的纸捻穿好固定,这时用自制的裁纸刀把纸一方方裁开,门钱的雏形出现在我们面前。剩下的就是凿刻图案。刻纸的凿子有十多把,刀形有圆的方的三角的,还有宽的窄的类似小铲的,目的是方便刻造不同的图案。除了凿子刻刀,其他的主要工具就是木制的垫板,上面涂了一层厚厚的松香和蜡。曹金祥告诉记者,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硬硬的木板崩坏凿刀的刃口,另外也是在刻制门钱时能准确的把握分寸。
凿刻之前,先用铅笔或炭条在门钱草样上打上九宫格,然后利用不同刃口的凿刀根据心中的图样刻制出不同的图案。曹金祥介绍说,这些图案多是一些吉祥祝福的图案,像五轱辘钱、梅花、双鱼、圆铲花等等,当然也能刻上祝福吉祥的字,像“新年快乐”,“庆贺丰收”等等,刻制完成的门钱抖掉纸屑,就成为半成品。
最后的工序就是染色。博兴一带的门钱用的颜色多是玫瑰红、品黄和品绿,把买来的颜料放在锅里用水加热,冷水泡开的颜料染色时穿不透厚厚的纸样,必须用热水颜料。颜色煮好后,把门钱草样的四边放在燃料里轻轻一蘸,在纸的吸附下,燃料慢慢渗入纸中,此时再用毛笔把刻制出的图案用不同的颜色轻轻点点,红黄绿三种颜色互相渗透在一起,形成五颜六色不同的色调。染好的门钱就可以拿出去挂在铁丝上、杆子上自然晾干。
等到充分干了,也差不多到了赶年集的时候,这时就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出售了。过不多久,家家户户的门楣上五颜六色的门钱就在鞭炮声中鲜艳地招摇着一年的吉祥与祝福。
曹金祥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博兴门钱的流行范围北至小营,东到广饶,南到桓台,西至高青,流行范围很小。过去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张贴门钱,从大门、屋门到窗户以致猪圈、粮囤,到处贴满了门钱,在风中招摇,甚是喜庆。
如今家家户户都修建瓷砖大门,门楣也换上了铝合金的,再用浆糊糊上门钱,就显得有点脏了。这是现在很多人家不贴春联乃至不贴门钱的原因。加上市场的萎缩,传统的门钱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曹金祥说,原来曹王二村尤其是村南的几个生产队,几百户,上千人,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刻制门钱,一年下来,哪家都能刻制二十几万幅门钱。而如今,刻染门钱的人越来越少了,村里现在刻制门钱最多的他,一年也就刻上十万来个。面对着这样的困境,老曹显得很是无奈。
邹平篇:五色门钱花枝招展
□朱庆光 李振平 田中岳
而在据博兴曹王镇曹二村不到一百里外的邹平县长山镇梁郭村,54岁的崔佃良也在日夜加班地赶制门钱。
梁郭村也是加工门钱的专业村,历史悠久,即便村里最老的人现在也说不上这门手艺的传承。据村支书介绍说,过去,村子里80户人家,有30户加工门钱,每到年前几个月的晚上,家家户户造门钱的声音持续通宵,不绝于耳。所以他笑言,每到这时候,村子里往往很少有贼光顾。
和曹金祥的门钱风格不同,崔佃良做门钱的纸用的是红、黄、绿、紫、粉红五色纸。原来需要自己买来纸,按颜色配好后,用大锤和铡刀来切割。而现在,邻县桓台陈庄有专门配纸卖纸的,只要一个电话过去,人家就会按着你要的尺寸把纸裁好送来。这让崔佃良感到很欣慰,毕竟,门钱是个季节性很强的手艺,赶时间多做才能赶到好时候卖个好价钱。因为省了一道重要的工序,老崔一年下来,能做100刀纸,百十万个门钱。
老崔做的门钱花样繁多,有狮子图案的、双鱼的、双喜的,灯笼的,还有刻有诸如“财源大发”等吉祥字样的。老崔告诉记者,不同的图案贴在不同的地方,像狮子图案的,只能贴在大门上,而猪圈上只要不贴鱼,贴啥都行。
和梁郭村做同样门钱的,还有桓台的两个村,和博兴曹金祥的刻染门钱一样,五色纸门钱流行的地域也很狭窄,据崔佃良说,贴这种门钱的地方,以桓台地面最为兴盛,东到邹平韩店,西到桓台唐山,南到张店的石桥、卫固一带,也就是几百平方公里的范围。
和日渐式微的博兴门钱不同,经济条件好的邹长桓地区,对民俗的传承似乎有发扬光大的趋势。老崔做门钱这么多年了,到现在也没有感觉出生产加工和销售数量比以前减少来。相反,很多地方的门钱尺寸随着大门的尺寸有见长的趋势。像老崔做的门钱就有10开和20开两种式样。据老崔说,在桓台唐山一带,还有人家用起了布做的门钱,气势大得很。
对于这种传统剪纸,村里人也在迎合人们不断变化的欣赏口味,赶制创新一些时髦的图样、字样。前几年,崔佃良就设计过带有紫荆花图案的门钱,销路也很好。
如今的崔佃良只需要再加埋头做门钱就行。过了腊月十五,自然就会有人过来批发门钱,省去了以前冒严寒东奔西跑赶集的麻烦。
从配纸裁纸,到刻制,最后到销售,传统的门钱工艺正突破原来那种自产自销的小农模式,抛弃那种繁琐的技艺,并不断有所创新,纳入到社会化大生产的洪流中去。或许这是五色纸门钱日益兴旺的原因。
记忆回响
门笺,门钱儿
□王长征
这种在研究资料里叫做“门笺”的玩意儿,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是叫做“门钱儿”的,到现在它也带着谜语般的絮絮低语,飘扬在古老时光的丝绸上……
其实这种飘飘扬扬的门钱儿,在北方的春节是非常普遍的吉祥之物,带着它轻轻的耳坠般可爱的儿化韵,像珠玉一样温润,说在嘴上,感动在心里。
在我的印象里还有一种东西的飘扬——那就是旗帜,那旗帜飘扬的时候发出了呼啦啦的声音,那旗帜指引的是浩荡的队伍,那旗帜下发生的都是些翻天覆地和惊心动魄的故事。门钱儿,这样的称谓就好玩了,这事儿就小了,小得成了玩意儿,没有了年关祭祀的沉重和满脸的禁忌了。它的絮絮,它的琐碎,尤其是它的飘扬,适合在心灵里珍藏,在梦里更加变幻莫测。当我们的家门上贴上这些飘扬的门钱的时候,那渴望已久的节日就来到了,那激荡的爆竹声就破除了漫长日子的沉寂。
到了除夕之日,那辞灶上天的灶王也就回来了,那祭祀祖先的香火也就点上了,那天地也敬了,那五谷也请了,那井水也拜了,那天井也一扫而光了,就剩下人间的福气与团圆,就撒满孩子们的欢乐了。
当我在依然料峭的寒风中抱来一摞红花绿沫的门钱儿,我奶奶就会从脑后的纂上拔下她佩带了多年的银簪子,将这些粘连在一起的方砖般的门钱儿一一拨开,这时它们才开始悉悉娑娑飘扬开来,我们就能依稀辨认出那被剪得歪歪扭扭的字眼,像些曲折的虫子,有“春满人间”,有“鸟语花香”,有“周而复始”,最好听的莫过于“招财进宝”了,别看我到现在还是过得清贫,可那时我们是多么盼着有一天忽然成为一位富有的人,腰缠万贯财大气粗地走向那个略带风尘的世界。
我知道春风就是从这里开始吹拂的,小小的蜘蛛从屋檐和树枝上坠着晶亮的丝线随风荡来了,它们又会在屋角的墙上开始织网,燕子衔着带叶的枝桠和温暖的河泥,呢喃着在我们的房梁上做巢。柳叶儿的眉毛,扬叶儿的耳朵,杏花儿的美人痣,桃花的芳心,披上铠甲的刺猬,一场蛇儿的虚惊,漏了狐狸尾巴……那雁阵的汉字,那黄蜂的丹青之巢蜗牛的笔墨之旅……那流水的欢笑跌跌宕宕,云又来了,雨又下了,日子又细水长流了,流着流着惆怅又来了,落花又带往东海,辛勤的耕耘,繁忙的收获,那时春联就褪色了,那门钱儿也找不到了,它已经被风吹得了无痕迹。
可现在不是还早吗?这猪年的门钱儿还正在剪着呢,那些门钱儿贴上门框的时候,那些日月般的对联也贴在两扇开开合合的大门上,百年不变的门枕、虎口里咬着的门环就有了红光,“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李笠翁的对句就被乡贤再次捻须而吟: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
现在我们就把消费剩下的零钱积攒下来,去买回你童年的门钱儿,让它们飘扬在我们古老的家门上,现在我们就写下浪漫的诗句:我们清贫,我们却穿着丝绸的衣裳,在春天的朝野里,我们周身闪耀着溪流的波光……